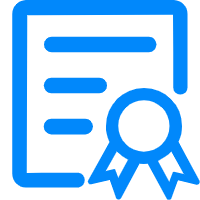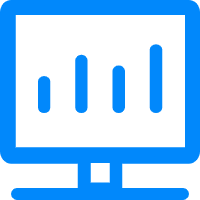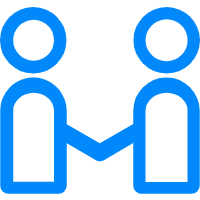在华东某科技城市,30岁的创业者孙磊经营着一家初创物流科技公司,专注于智能配送系统开发。2023年秋,他与一家大型电商平台“迅达科技”达成合作意向,双方草签了一份临时协议,约定孙磊提供一套定制化配送软件,费用100万元。协议看似简单,却因效力争议,将孙磊的公司推向了破产边缘,卷入了一场合同效力纠纷的法律漩涡。
故事的开端:临时协议的诱惑
孙磊是在一次行业论坛上认识迅达科技的项目经理王某的。王某表示,公司急需一套高效的配送软件,愿意支付100万元,但因项目紧急,只签了一份“合作意向书”,注明费用、交付时间(3个月)及主要功能,承诺后续补签正式合同。协议虽未加盖公章,但有王某的签名及迅达科技的电子邮件确认。孙磊觉得对方是大企业,信誉有保障,便投入全部资源,组建团队加班开发。
两个月后,软件初版完成,孙磊将演示版本发给王某,得到对方高度评价。然而,验收前,王某突然告知,迅达高层认为项目预算超标,决定暂停合作,拒绝支付任何费用。孙磊傻眼了,他的公司为这个项目已投入80万元,包括服务器租赁、员工薪资和外包费用。他多次联系王某要求补签合同或支付费用,却被推说“意向书不具法律效力”,迅达不承认债务。
纠纷爆发:效力的争议
孙磊无法接受。他认为意向书虽未正式化,但双方已实际履行,应视为有效合同。无奈之下,他委托律师向法院提起诉讼,以合同效力纠纷为由,要求确认意向书为有效合同,迅达支付100万元费用及违约金20万元。他提交了意向书、邮件往来、软件演示记录及与王某的微信对话,证明双方存在明确合意及部分履行事实。律师援引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136条,强调书面合同形式不影响合意成立,意向书具备合同要件,应受法律保护。
迅达科技则辩称,意向书仅为初步洽谈文件,未经公司盖章,无约束力,且孙磊未交付最终产品,无权索款。他们提交了公司内部审批记录,称王某未经授权擅自签署意向书,迅达不应担责。庭审焦点很快集中于意向书的法律效力及王某的代理权限。
法庭交锋:合意与授权
孙磊的律师出示了迅达科技的官网宣传及王某的名片,证明王某以“项目经理”身份对外洽谈,构成表见代理,迅达应对其行为负责。微信记录显示,王某多次确认“项目继续推进”,并要求孙磊修改功能,表明双方已进入履行阶段。迅达则坚称,意向书仅为“意向”,未明确权利义务,且公司内部规定大额合同需高层审批,王某的行为无效。
法院调查发现,迅达曾通过邮件确认接收演示版本,并提出具体修改意见,足以证明其认可协议内容。法官依据《民法典》第502条,认定意向书虽形式不完备,但具备要约与承诺,构成有效合同;王某的行为符合表见代理规则,迅达需承担责任。2024年6月,法院判决确认意向书有效,迅达支付孙磊80万元(按实际投入计算)及违约金10万元,总计90万元。
结局与代价
判决虽胜,孙磊却未能挽回公司。诉讼期间,资金链断裂导致团队解散,他个人背上50万元债务。执行阶段,迅达虽支付了部分款项,但仅40万元到账,剩余因公司“资金调度”一拖再拖。“我以为大公司讲信用,没想到连张纸都信不过。”孙磊说。而迅达则继续运营,丝毫不受影响。
这起合同效力纠纷揭露了临时协议的法律风险。看似简单的意向书,可能隐藏效力争议的雷区。法律为孙磊正名,却无法弥补他的创业梦想。在商海中,合同不仅是合作的起点,更是博弈的底线。孙磊的故事提醒每一个创业者:签字前多一分谨慎,或许能少一分悔恨。